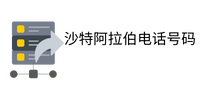“杀死普通话” [1] :5 月 9 日离我们而去的琳达·黎 (Linda Lê) 通过一场语言犯罪——她的母语越南语——呈现了主导她写作的行为:选择用外语写书,而且只用这种语言——法语 己的文字 。
琳达·黎 (Linda Lê) 于 1963 年出生于越南大叻,1969 年为逃避战争与家人前往西贡。她继续在法国一所高中接受教育,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对法国文学的热爱,不仅包括法国文学的结构,还有法国文学的声音和歌唱。
十四岁那年,西贡沦陷、共产主义胜利后,琳达·黎 (Linda Lê) 与母亲和妹妹离开越南,定居法国,留下了她再也没有见过的父亲。除了这一痛苦事件的记忆之外,她还会想起那些萦绕在她脑海中的幻觉——她在小说中对此毫不掩饰——因为害怕遭到告发,她决定尽快处理掉她珍藏的法国文学书籍,这些书籍 被她的国家的“文化净化者” [2]视为“堕落文学”。与此同时,她将做出一个彻底的决定,永远不再说她的母语。
从她与法国文学语言的接触中
她可以说“她拥有它”,并且正是由于它,她才能够“一笔勾掉自己的传记” [3]。
琳达·勒 (Linda Lê) 的写作既博学又华丽,同时也颇具腐蚀性和讽刺意味,她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中充满了这种持续不断的斗争,既有对母语的背叛感,也有选择法语作为庇护的选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自己的 阿尔及利亚电话号码库 写作” [4]的发明才成为可能。他的作品交织着这种张力:一方面,他因为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父亲而发出难以忍受的自责之声,另一方面,他又在写作中感受到“狂怒”的喜悦。
但除了这一令她心碎的选择所带来的痛苦之外,琳达·勒的写作还发挥了她母语中神秘的沙沙声响,就像乔伊斯式的顿悟一样。 “你能用一种非自己的语言进行发明创造吗?我决定冒险一试。我敢创造新词……” [5]
Linda Lê 通过使用新词找到了一种应对这些语言 为何贸易展会如此受欢迎 现象的方法,即把它们注入法语中,同时也找到了一种破坏法语规则、使法语变形的方法,即通过产生非常有创意的语言形象。 “自从1997 年写下《三个命运》以来,我已经从玩弄语言和在同一本书中介绍不同层次的语言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既有非常正式的语言,也有俚语” [6],这表明这个游戏对她来说,不是“练习的,而是必要的” [7]。
通过发明独特的写作过程
Linda Lê 成功地将这些语言沙沙声的回声转化为保留了闯入特征的美学作品。换句话说,这位作者对这封信的处理并不涉及语言的他者,而是通过创造行为的力量对谜团做出回应——其效果是现实的、享受的,这一点从她独特的风格中可以看出来。
媒体曾多次试图将琳达·乐 (Linda Le) 描绘成越南流亡群体苦难的代言人,但林达·乐始终没有接受。在各种采访中,她谈到了自己对被身份认同所困的恐惧,而写作使她得以逃脱:“感觉自己像个外国人还是很有好 哥斯达黎加商业指南 处的”,她可以用微妙的讽刺来回应,这种讽刺定义了她自己 [8]。
她将把波德莱尔的这句诗变成“深入未知的深处去寻找新的 东西!” » [9]她的艺术之家 [10]把她与她的“坚实盟友”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与这样的选择相一致:除了流亡的语言之外,没有其他可能的存在,而流亡者发明了这种语言,并总是重新开始。